2014/01/03 | 來源:解放日報《藝術(shù)家具》專版
[摘要]在明式家具故鄉(xiāng)蘇州��,至今還留存不少明式家具的珍品,比起一些流散在各地的遺物來看���,無疑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如今仍保存在姑蘇城外西園戒幢律寺的那件大案桌����,就是極其典型的實例�����,也早已聞名遐邇,為世人所器重�����。
在明式家具故鄉(xiāng)蘇州���,至今還留存不少明式家具的珍品�,比起一些流散在各地的遺物來看��,無疑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如今仍保存在姑蘇城外西園戒幢律寺的那件大案桌�,就是極其典型的實例,也早已聞名遐邇��,為世人所器重����,只是一直未見有實物圖像或文字資料的說明和介紹。2000年春節(jié)期間��,筆者有緣與西園寺住持普仁法師認識��,再次飽賞了寶物之古韻,并征得法師的同意���,還拍攝了幾張照片�����。

這件珍貴的大案桌�,按北方古董行業(yè)中的分類�,一般稱它為“平頭案”,因其腿足收進�����,桌面兩端外伸有拋頭����,屬所謂“案形結(jié)體”。但在蘇州和江浙一帶���,不管腿足收進還是裝置在四角,一般皆不稱為案而稱之為桌����,或俗稱叫“臺子”。由于此大案桌采用的是一種特別的包鑲作法���,在案桌的表面鑲貼了一層老花梨(北方俗稱黃花梨)的木片�����,木片厚0.4厘米��,形狀大小不等�����,據(jù)有人統(tǒng)計����,整個案桌共用木片2930片,拼鑲成冰綻紋�,故蘇州人都稱這件大案桌叫“千拼臺”。這種冰綻紋的裝飾十分類似古時僧人穿的“百衲”袈裟��,又長期深藏古寺舊殿之中�,因此,我們也可名其為“百衲桌”�����。
百衲桌的珍奇之處,也正在這里����,不僅造型比一般明式家具還簡練、純樸���,而且不起任何凹凸或方圓的線腳�����,所用構(gòu)件皆方正�、質(zhì)素����、單純。稍遠望去��,全然憑藉用料料份的寬窄與厚薄的合度�,以及形體各部分之間比例的和諧協(xié)調(diào),給人造成強烈的形式感�����,故顯得格外的莊重�����、敦實��、大氣����。古拙的形體和清澈的骨相,著實讓你感到一種震撼���,有著神奇般的誘惑力��,從而�����,使人悠然產(chǎn)生無比的振奮和美感��。
當(dāng)人們臨近大案桌時�����,則會情不自禁地對巧奪天工的“百衲”冰綻紋(也叫冰裂紋����,冰片紋)包鑲工藝贊嘆不已,天然木質(zhì)紋理在組合���、拼鑲的變幻中處處顯出精美和典雅��。歷經(jīng)了幾百年的流傳��,至今紋絲未動�,每塊鑲片仍平伏貼緊���,完好無損��。這種工藝貌似簡單����,但從設(shè)計���、畫樣�����、裁割到拼貼��,無不體現(xiàn)出古時匠師高超卓越的技藝水平��,也是明清時期蘇州“細木”工藝之一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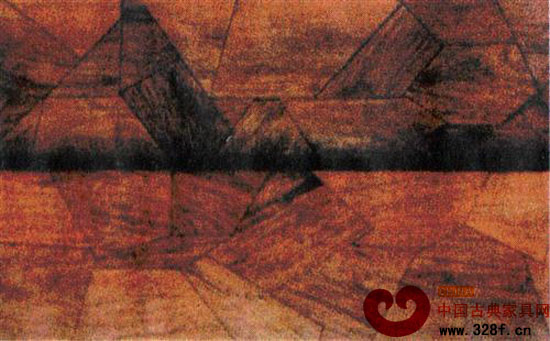
這件案桌之大����,著實令人刮目相看�����,其桌面長340厘米�����,寬91厘米����,在所知的明清古典家具中,極為罕見�����。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鐵力木翹頭天然幾�����,長達343厘米,但寬僅50厘米����,比西園寺百衲桌要窄41厘米;上海博物館也藏有一件老花梨木的平頭大案桌�����,長有350厘米�����,但寬也僅62.7厘米����,仍窄27.3厘米,這三件案桌的高度大致接近�,只因桌面寬窄不同,呈現(xiàn)的氣派也就大相徑庭���,西園寺的百衲桌顯得更淳樸��、厚拙����、大度,不同凡響����。根據(jù)北方工匠所謂“窄長桌案”與
“寬長桌案”的區(qū)分�����,此大案桌似乎屬“畫案”類��,兩個博物館的案桌則歸屬“條案”類���。然而���,無論從這件百衲桌的形體尺度,形制規(guī)格����,還是“百衲”形式的裝飾意圖來看,不像是專供書畫使用的家具����。不是一般的所謂畫案或畫桌����,應(yīng)更有其造物的目的和功能要求�。像這樣一件材美工巧的大型案桌,一定是為了適應(yīng)一種大場面�,為了某種特殊的使用目的,才去如此構(gòu)建并實現(xiàn)其完美形象的��。我們不難想象����,桌上可以擺放大量物品,在特定的環(huán)境中一定被安排在一個中心位置����,或者非常顯要的地位。若不是大戶富家����,沒有面廣三間的大廳堂,是無法容納和相稱的;如果擺在佛殿上�,一定會是用作供奉佛祖,陳設(shè)供品�,或供作佛事之類的家具,其特別的使用意義似乎相當(dāng)明顯。
據(jù)文獻記載�,西園寺創(chuàng)建于元代至元年間(1264—1294),始名明元寺��。至明代嘉靖(1522—1566) 之末���,由太仆寺卿徐泰時構(gòu)筑東園時���,把已經(jīng)衰落的寺址改建成了宅園,改名西園��。徐氏故世后�,其子徐溶又合園為寺�����,并于崇禎八年(1635)�����,延請報國禪寺茂林律師任住持�,則名為戒幢律寺。后漸成法會盛地��,名列江南首剎。但于清咸豐十年(1860)����,毀于兵燹,至光緒年間又再度修復(fù)�����。這段歷史��,雖然不足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件百衲桌是否與西園或西園寺有什么直接關(guān)系�����,但也可說明十六世紀中葉以后�,蘇州大批園林的建造和明清時期號稱“蘇州時代”的歷史條件,才導(dǎo)致了明式家具的形成和發(fā)展��,才能出現(xiàn)如此出類拔萃的創(chuàng)造�。